制定脑类器官研究伦理的新紧迫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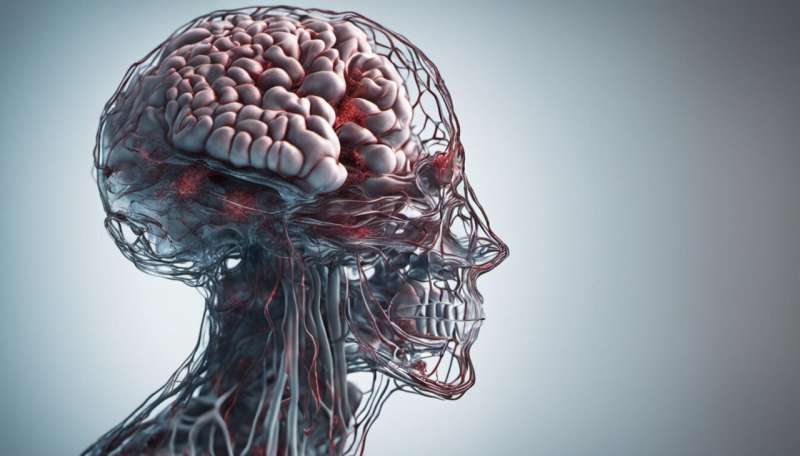
科学家们越来越擅长制造大脑类器官——本质上是在实验室里用干细胞培育出的微型人脑。
尽管大脑类器官研究可能看起来很古怪,但它有一个重要的道德目的。除其他好处外,它有望帮助我们理解早期大脑发育还有神经发育障碍,比如小头畸形、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
但大脑类器官研究也引发了严重的伦理问题。主要的担忧是,大脑类器官有一天可能会获得意识——这一问题刚刚被一项新的科学突破推向前台。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人员最近发表创造出能自发产生类似早产儿脑电波的脑类器官。虽然这电活动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类器官是有意识的,它确实表明我们需要尽早思考伦理问题。
监管漏洞
干细胞研究已经受到严格的监管。然而,现有的监管框架还没有跟上与大脑类器官相关的独特的伦理问题。
比如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指导方针bob88体育平台登录全国人类研究伦理行为声明保护那些捐赠人类生物材料用于研究的人的利益(同时也解决一系列其他问题)。但他们没有考虑大脑类器官本身是否可以获得与道德相关的利益。
这一差距并非没有引起注意。一个日益增长的的数量评论员认为,脑类器官研究应该面临比适用于干细胞研究更普遍的限制。不幸的是,在确定这些限制应该采取什么形式方面,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意识与道德地位
我们首先需要考虑意识的道德意义。意识在道德上很重要。这是主要原因为什么我们对待人类、大象或兔子要比对待石头更小心?人类、大象和兔子都是人的意识.岩石则不然。
但并非所有有意识的生物都有同等的道德地位。
道德地位的最高境界是留给“人”的。人格通常被认为需要复杂的认知能力,如自主性、道德能动性或复杂形式的自我意识。
正常的成年人也是人。一些非人类动物——比如黑猩猩——可能也符合这一要求。
有意识的类脑器官几乎肯定缺乏相关的能力。然而,作为有意识的人,他们的利益仍然很重要。作为第一位动物解放主义者杰里米·边沁他在18世纪说:“问题不在于‘他们会推理吗?也不是“他们会说话吗?”而是‘他们会痛苦吗?’”
这是一个重要的门槛。我们应该限制可以用有意识(但不是无意识)的脑类器官进行的研究种类。我们应该确保有意识的类脑器官的利益得到考虑。例如,我们应该要求研究人员既要说明为什么不能使用无意识的类器官进行研究,又要积极地将自己的痛苦和折磨降到最低。
我们还需要一些筛选意识的方法。一种选择是限制与怀孕20周以上胎儿大脑相似的脑类器官的研究最早的意识形成时间在人类身上。
另一种选择是直接测量与意识相关的大脑过程.我们应该通过在意识方面犯错来解决不确定性;把一个无意识的大脑器官当作有意识的来对待,通常比犯相反的错误要好得多。
超越意识的道德地位
有一类研究引发了额外的道德担忧:类器官可以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
研究人员开始将大脑类器官连接到机器人身体而且在非人类动物的大脑中植入类脑器官.认为这样的生物可以发展出比局限于细胞培养的类器官更丰富的精神生活,这并不牵强。
我们应该对这些人进行筛选,以发现他们意想不到的认知能力,试着理解这些人的美好生活是由什么构成的——并相应地对待他们。我们不应该假设它们是某种“生物机器”。
我们还应该考虑他们的道德地位的程度。如果这些类器官发展出超越意识的复杂认知能力——例如,如果它们表现出自我意识的形式——我们可能想要格外重视它们的兴趣,甚至完全排除有害的实验。
让我们高估道德地位
我们可能不知道特定的大脑器官是否具有特定的认知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低估了他们的心智成熟度,我们就有犯下严重道德错误的风险。因此,我们应该高估而不是低估道德地位。
这只是一个可能的监管框架的粗略轮廓。关于我们应该如何治疗拥有意识自我意识或其他认知能力。
然而,随着前景的意识大脑类器官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我们现在需要开始这个对话。
科学正在创造新的生命物质。随着权力而来的是责任,重要的是道德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



















